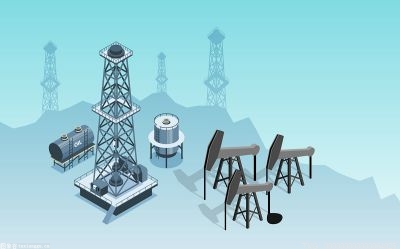龚曙光:两三面——追思黄永玉先生
文/龚曙光
黄老走了!走得爽快、利落,也走得突然、意外。分明就要跨过百岁之门了,可他偏偏止步在了门边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意外归意外,这的确就是属于黄老的走法。这老头儿,一辈子无论做什么,但凡算件事,他都要做得出人意外,弄得满世界一惊一乍,何况辞世这么一件人生大事,当然更得把戏份做足。前不久,他还在为自己的“百岁画展”作“官宣”:百岁百画,全为新作,且比过去好!他要为这百岁华诞,献上一份体面的自寿之礼。相识与不相识、相关与不相关的人们,备好了心情和掌声,正要为他的下一个百年人生喝彩祝福,他却突然一转身,用一个永远少年的背影,以及不留存骨灰、不聚会追思的叮嘱,谢幕在所有人的惊诧、遗憾和不舍中,留下一路爽朗而诡谲的笑声……
我见黄老次数不少,但真正面对面坐下来,说事谈艺或聊天,其实只有两三回。
初次见黄老,是在他建好不久的夺翠楼。那时我还在湘西,听说他回了凤凰老家,便冒冒失失邀了朋友前去拜访。因为没预约,起初他明显不热情,但一听说我喜欢他的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,立马让坐看茶,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。论年龄,他已的确是个老头儿,可那思维、才情、语速和神态,又分明是个少年。你弄不清他究竟是童心未泯,还是返老还童,反正他会用一团滚烫的青春气息,鼓荡得你心神飞扬。
我们从这部他刚刚开头的小说聊起,不一会便天南地北了。他聊得最绘声绘色的,是意大利、翡冷翠、洛伦佐和文艺复兴,还有美食、时装、足球、赛车、冲浪、歌剧和美女。那时我没出过国,更没到过意大利,所有的印象,全来自徐志摩、朱自清的诗与文。黄老聊天,爱讲小故事、小感受,很少作提炼归纳,听他激情澎湃讲了一上午,仍不明白欧洲之大,他何以独宠意大利。直到后来我去了那里,才明白这座人类的“欲望花园”,实在太契合黄老的性情与气质,若就艺术的绚烂和人生的灿烂言,确实没有比翡冷翠更适合他居住的地方了。
与黄老再次见面,是在长沙的喜来登酒店。我宴请他,是为了商定《黄永玉全集》的编辑体例。当年湖南美术社出齐《齐白石全集》,停下来不知道再出谁。我提出要将“全集”做成一个系列和品牌,把那些在世的大师做进来。于是《吴冠中全集》《黄永玉全集》便列入了出版计划。
黄老全集的编辑中,主要的分歧是文学创作进不进。主张不进的是李辉,他的理由是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沒写完,当然还有文学版权难以征集。主张一定要进的是我,我认为黄老的成就,美术与文学参半,究竟孰主孰次,目前难以判断。如果去掉文学,这套书只能叫《黄永玉美术全集》,不能叫《黄永玉全集》。黄老原本两可,听我说要改书名,便表态将文学创作收进去,编作美术卷和文学卷。
也就是那次见面,定下了精装版用小羊皮做封面。黄老说小羊皮他自己去意大利挑,要用就用最好的。后来印制的200套精装书,用的就是黄老挑选的小羊皮。原以为每套12万的订价会曲高和寡,没想到比平装书还销得快。
最后一次见黄老,是十年前。再过几天,就是黄老九十岁的生日了,我们将《黄永玉全集》赶了出来,作为一份寿礼奉上。
那天的新书发布会,设在北京饭店贵宾楼。地点是黄老定的,他似乎一直喜欢那里。下午,阳光灿烂而不燥热。黄老穿着橙红色的衬衣,淡黄色的西装,配了一条银灰细花的领带,正式而不失活泼,颇见配搭的用心。我没想到他会穿西装,因为一般美术界的活动,无论多隆重,着装都随意。我是特地挑了一条蓝牛仔裤配白丅恤,免得西装革履格格不入。见黄老装得正式,我连忙向他道歉。他听了哈哈大笑,说衣服是穿给自己的,适合自己就好。人若不对路,穿同款也有违和感。
我们又聊起《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》。我说那种慢镜头似的叙事,如同普鲁斯特,让你看得到时光流淌的样子。黄老说那你是真看进去了,我虽无意于模仿谁,但喜欢“时光流淌的样子”这句话。写生命,就是要写出时光流淌的样子,绘画做不到这一点,即使是画历史题材。这也是我坚持文学写作的原因。
首发式由我主持,这是我在出版集团任上唯一一次主持新书发布。其间有一场简短的对谈,我只谈了文学,美术则不敢班门弄斧,毕竟这是在谈论一位跨世纪的大艺术家,不是朋友间的相互捧场。我知道在四大名著中,黄老并不偏爱《红楼梦》,可我依旧说他的长篇,是当代最具“红楼”式雍容大气、淡定舒卷的小说,不管将来还得写多少卷,业已完成的部分,堪称20世纪中国的宏大史诗。这样的判断,必定会招惹争议,但我既然如此认定,就不惧怕如此发布。
会后,黄老邀请我参加他的九十寿宴,可恰好我要出国,去的又是意大利,错过了一次目睹黄老风采的绝佳机会。
两三面的交往,够不上知人论世,也达不到知世论人,更何况,黄老本就是一个多面多彩的“庞然大物”,非寻常目光可以尽览和洞穿。我只是觉得,他是一个生命与才情澎湃的稀有物种、濒危物种,他这一走,或许这个物种便消失了。一个时代,无论是熔炉还是炼狱,总会锤炼出几颗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匾、炒不爆、响珰珰的铜碗豆。黄老就在这一百年里,被颠扑折腾的时代炼成了一颗铜碗豆!他仗恃才华却又糟践才华,每每用才华戏弄时代;他入世很深却又出世很远,每每用出世姿态入世;他心怀善意却又出语刻薄,每每用刻薄言辞表达善意;他质本乡愿却又耽于时尚,每每用时尚审美张扬乡愿;他心仪于民国却又得意于当下,每每用当下的生活演绎民国的风范。黄老或许是唯一一个以民国风尚和作派活在当下,且风生水起的大艺术家。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大家,人虽跨入了当代,气质与作派却丟在了民国,将自己的人生,活成了风格迥异的两个版本,包括他的表叔沈从文。只有他无论时运顺悖,都能我行我素,将每段岁月都活成自己的时代,将每块土地都踢成自己的主场。
我们对于黄老的伤逝,或许不只是对一个具体生命的哀婉与追忆,还是对一种时代风尚的怀念与祭悼,更是对一种人生梦想的祝福与守护……
2023年6月15日
于抱朴庐息壤斋
来源:红网